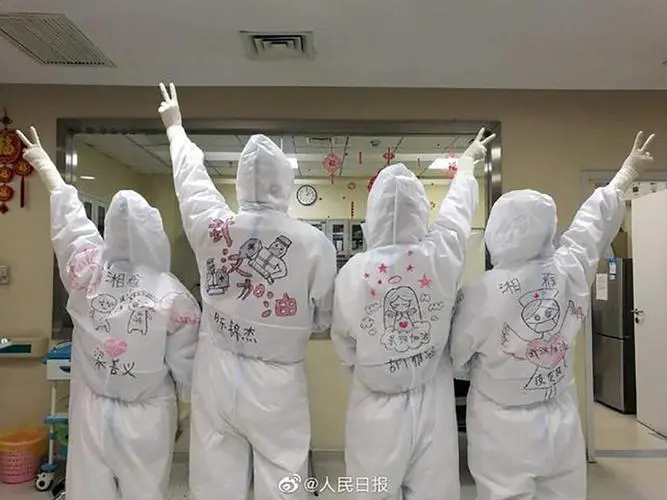创造学思想录```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相信我,这个对你有帮助! 一:论人的伟大——《思想录》节选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二:《建筑师的思想录 》这本谈建筑的书,如果你把它当作哲学书来读,也许更合适。这么说,实际上是假定谈建筑的书与哲学书应当有所区分。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这个假定的确是存在的。建筑究竟应该怎么谈?我(们)未必清楚,不过,张永和还是使我(们)产生了疑惑:竟然这样谈建筑,可以吗?不可以吗? 显然,张永和了解这种疑惑,要不,他不会把自己的工作室叫做“非常建筑”。在汉语中,“非常”这个词值得玩味,它的字面意思是“不同寻常”,有一部电影,中译作“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跟原片名完全相反,但与内容却十分贴切,是很好的意译。“非常”的另一个习惯用法则是作程度副词,相当于“很”、“十分”。这样,“非常”的前一个意思是表示与usual相反,也就是unusual;而后一个意思则是表示比usual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more than usual。这是汉语多义或模糊的又一个例子。 回到“非常建筑”这个话题,我们既可以把它理解为unusual architecture,也可以把它理解为very architecture。前一种理解,可以说是站在一种外在的立场;后一种理解,也许更符合张永和自己的立场。事实上,“非常建筑工作室”的作品集出版,他把书名先后取为“非常建筑”(1996)和“平常建筑”(2002)。 从非常建筑到平常建筑乃至基本建筑,不能不说其中有深意存焉。张永和后来更多用“平常建筑”以及“基本建筑”这些提法,这是基于他对建筑本质越来越趋于删繁就简的理解:建筑实践意味着面临如何理解、限定、设计、研究建筑等等问题,而如果把建筑动词化,这些问题即可简化为“如何建筑?”(如何盖房子?)。 全书由长短不一的三十多篇文字构成,短的几百字,最长的也不过万把字,即使是长文,相信读者也不会把它混同于那些发表在Journal上的论文,我想,这自然是因为作者采用了一种格言或断片式的写作方式,简洁、跳跃、质地密集,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那些著名的哲学笔记。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1982—2004。作者的身份从加州伯克利分校建筑系的研究生到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而风格(语言以及思维倾向)似乎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将最早的《自行车(的故事)》与最晚的《我的红楼梦,或三考》做一比较,如果不看写作日期,你想不到这中间隔了二十二年。这似乎又一次应证了我的一个观念:人的重要品质在二十几岁就已形成,之后的学习与经历作用甚微。 作为一名教师,张永和有机会把自己对建筑的独特理解灌输给学生,因此,从他有关建筑教育的论述——主要是《四函》与《关于建筑教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建筑理念。 《四函》写于1985年,时作者在美国印地安纳州的保尔州立大学建筑系教大学二年级的设计课,这四封信所录的是他写给学生的设计任务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任务书没有向学生布置什么技术性指标,而是引导学生对建筑基本概念进行反思。第一封信——练习,要求学生研究生活事件与人造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提醒学生重视细节。第二封信——过程,告诉学生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并传授给他们一个经验,那就是:在练习时坚持做笔记,把所有的思考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事实上,张永和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收在本书中的很多篇文字就是他的思考素描。有关过程的思想,后来他有进一步的发挥,参见写于1988年的《过程思想》。第三封信——舞台,教导学生建筑不过是提供我们行为发生的一个背景或舞台,设计必须为人的活动服务。第四封信——经历,这封信是这门课的总结,鼓励学生向自己的经理学习,并提供给学生三件工具:一是写作,给所设计的方案加上一段不相干的故事或剧情;二是把一个局部或一个细节作为设计的起点;三是绘图必须具体,要十分注意细节。通过这门课,张永和旨在卸下学生的思想包袱,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对建筑及其设计的理解。 《关于建筑教育》写于2001年,时作者在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事,其中不仅有对以美术为基础的传统建筑教育的全面反思,还有对新建筑教育模式的积极建构,依我看,是中国建筑教育的一份划时代文献。在文中,张永和放胆倡言,要重新定义建筑学基础:美术不是建筑学的基础,建筑学的基础是基本设计活动(思维),取代建筑专业美术基础课的是艺术修养的培养,而艺术范畴不局限于绘画、雕刻与设计,应涉及电影、戏剧等诸多领域。事实上,张永和本人就有很好的艺术素养,他对世界电影、文学、绘画作品了解之广、理解之深,令人惊叹,读者只要细按《文学与建筑》、《文学与空间》两篇自可判断,毋庸在此多言。 如果说传统建筑教育理解下的建筑是一种美术建筑,那么,张永和所提倡的建筑也许可以称之为观念或理论建筑。必须说,这种想法并非他一个人的发明,早在1982年访问匡溪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建筑系时,他就与“理论建筑”相遇而大受刺激,详《匡溪行》篇。而在国人中亦不乏友声:台湾著名建筑学家汉宝德(1934— )在1980年代即云:“也许建筑根本就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个思想的范畴。如果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也许可以把建筑家定义为思想家。”(《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16页) 张永和当然是一个建筑师,并且是在美国注册的建筑师。他也要盖房子,他也要与雇主打交道,在这些方面,他与一般建筑师没什么两样。但是,在他身上,你总会感到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不同呢?不错,他在名牌大学读书教书(2002年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下健三讲座教席,2005年9月起MIT建筑系主任),他获得各种国际大奖(1987年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第一名,1996年美国进步建筑优秀建筑工程设计奖,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2004年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但这恐怕都不是什么要紧的,要我说,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一般的建筑师满足于作为工匠,而张永和则梦想成为能思想的工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本书就是他的《思想录》。 帕斯卡说,人是一支会思考的芦苇。昆德拉则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我知道,现实是,不思考的人、不会思考的人是多么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