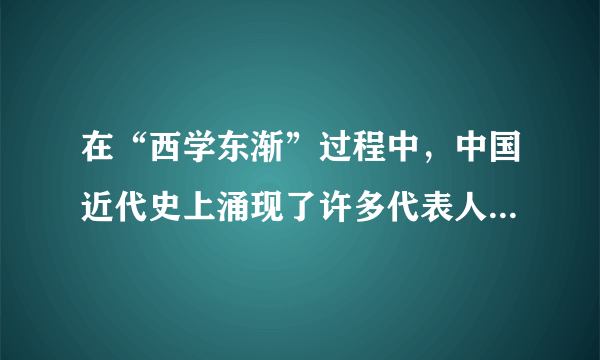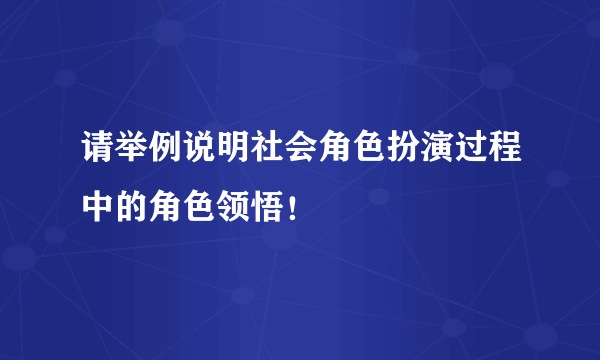别连科的叛逃过程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别连科的刑事案件材料及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交待,再现了他1976年9月6日逃跑的新闻细节。
12时50分,米格-25起飞。到达一定高度后别连科关掉了加力,以节约燃油。他没有按飞行任务的要求返回邱谷耶夫卡机场,而是飞向了东南方。
别连科由高度8000米猛“跌到”了1000米,并继续降低高度,以保护自己免遭日本雷达捕获及日方防空武器的突然袭击,然后按动了告急按钮——飞机开始发出连续的呼救信号。随后别连科关掉了按钮,以造成一个印象:飞机失事了。他还关掉了雷达设备和其他产生辐射的电子仪表——这有助于发现飞机的方位。
30分钟后,别连科已到达日本北海道地区上空。美国的“鬼怪”飞机在这里巡逻。驾驶‘米格”机的别连科希望被发现并引导着陆。日本防空作战值班员命令值班飞机予以拦截。一段时间美国的“鬼怪”飞机已标出了苏联飞机的方位并试图迫使它着陆。但因高度太低,别连科的“米格”机从雷达上消失了,“鬼怪”飞机失去了目标。
别连科继续降低高度、当高度为250米时,他看到了飞机场。这就是日本的函馆民用机场。距离南面别连科起初想降落的空军基地有150公里。米格-25试图降落时,航线上出现了正在起飞的日本波音-727客机。歼击机上燃料指示已经为零,二次降落的设想被排除了。为避免同“波音”飞机相撞,别连科急转弯贴向地面,并以每小时360公里的速度冲向跑道。之后他启动了制动伞并开始减速,飞机冲出了跑道,在地面犁出了一条沟痕后停在了金属天线前。除机首轮胎的前罩破裂外.并无其他损伤。油箱内所剩燃油总共还能维持30秒。时钟指示为13时36分… 日本 。
别连科扯下氧气面罩,取下降落伞,由驾驶舱爬到了机翼上。几辆汽车朝他飞驰而来,由车内跳出了手持相机的人。别连科向他们打手势,要他们收起相机,但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时他拔出手枪,朝天连开了数枪。相机立即收藏了起来,有人甚至还取出了胶卷,将其扔向地面。一辆汽车驶近飞机,车内钻出了两个打小白旗的人。其中一个操着蹩脚的俄语请别连科收起手枪,并把手枪和刀具交出来。别连科照办了。
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一官员叙述说:我们让别连科坐进汽车,把他送到了候机楼主任办公室。很快。我们的一位俄语讲得不错的工作人员来了,他自称是日本外交部人员,但别连科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情报官员。飞行员递上了便条。
我们问俄罗斯人:“您偏离航线了?”
“不,我是有意飞到这里来的。我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请把飞机盖好,派人保护起来。我要立即同美国人取得联系。”
“好的,跟我们来。”
别连科被带到了走廊上,那里聚集了一群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为了遮人耳目,别连科用上衣遮住了脸,仅留下了一条缝隙看地面。随后我们就把他带到机场宾馆,安排他住进了有两名保卫人员监视的房间。此外还留两人在房间外面守卫。不久就有人给别连科送来了衣服、鞋子和午餐,可他想要啤酒,但遭到了拒绝。
“根据可以理解的情况,我们暂不能向您提供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忍耐一下吧,一切都会有的。”
别连科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请他详细讲述飞行的细节和目的,他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但同时也要求我们把降落伞和飞行服扔进大海,以“造成飞机坠海的假象”。
我们的代表拒绝了这样做。他告诉别连科,俄国人已知道他在日本,且要求返还驾驶员和飞机......
当天,日本政府的工作人员试图向苏联驻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转交米格-25飞机驾驶员书写的声明:“兹证明本人,维克多·依万诺维奇·别连科不愿返回苏联,希望得到允许在美国定居。该决定由本人自愿做出,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维克多·别连科。”
大使断然拒绝接受这一文件。就在这天,莫斯科指控东京向似乎偏离航线的苏联飞行员提供了麻醉剂。苏联外交部向日本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立即交出驾驶员和飞机。
翌日,别连科被送往东京。行前,为找着一身合体的西服更换而花了很长时间。早晨,宾馆附近聚集了一群记者。特别机构的官员决定从楼房不为人注目的侧门将飞行员带出。记者识破了这一手腕,安全人员好不容易才把别连科推进了汽车,然后开足马力驶离院子。记者们却穷追不舍。情报机构对事态的这一发展早有所料,在一个十字路口,另有6部一模一样的汽车正在等候载有别连科的汽车。这些汽车眨眼工夫混在了一起,行驶了若干时间后,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分道扬镜,向4个方向驶去……
别连科乘坐的汽车终于来到郊外垃圾场,一架直升机随即降下,一分钟后它又升入空中,并向南面的空军基地飞去。
别连科在那里换乘了军用运输机,大约40分钟后降落在了东京机场。他被送往海军基地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正在那里等候。他说:“我叫吉姆,我代表美国政府。我受权通知您,美国总统将满足您政治避难的要求。手续一旦办妥,我们就飞往美国。”
然后日本人把别连科送入了监狱,一再致歉说:“这在日本是最安全的场所......”
在牢房,别连科享受了特别提供的膳食和饮料,甚至还得到了啤酒。次日清晨,日本按计划演出了一场戏。
多次同别连科会面的美国记者约翰·巴朗回忆说:日本人向别连科隐瞒了因他违反日本法律将要出庭受审的消息。他被带进了法庭,身着长袍的法官宣读了正式起诉书:“您被起诉违犯了日本法律的4个条款:您非法侵犯了我国领空;没有签证来到了我国;携带有手枪;进行了射击。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是的。”
“您为什么没有签证?”
“要是我申请签证,我将终生被监禁。”
“您为什么把手枪带到了日本?”
“手枪是我装备的一部分,没有手枪我不会被允许飞行。”
“您为什么要开枪?”
“为的是不让有可能损坏飞机的人靠近它。这架飞机非常宝贵。”
“您是否准备签字,承认在被起诉的这些条款上有罪?”
“如果您有此要求的话。”
“我决定,”法官宣布,“这是一个不应惩罚的特殊案例。别怕,我们不打算破坏您的计划……”
正式程序结束了。法官微笑着握了被告的手,请翻译祝他一切顺利。
与此同时,苏联当局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行动来谋求遣返别连科。日本人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使本已不睦的苏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日本政府举行的秘密会议上,作出了安排别连科同苏联驻日使馆代表会面的决定。叛逃者——别连科接到这一通知时感到局促不安:“要是我拒绝同他见面呢?”
“那我们就通知苏联代表,说你不愿见他。不过事态的这种转变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日本人认为会面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克格勃代表”有从肉体上消灭叛逃军官的可能。因此,会见厅里组织了预演。3名武装警卫的眼睛将直盯着别连科,另3名紧盯大使馆代表。如会见失败,必要时他们都有权开枪。
会见前数小时,别连科已熟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吉姆会见了他,为他“壮了胆”。同别连科告别时,美国人干脆利索地亮出了最有力的王牌:“如您照我们的建议去做,几小时后我们就可飞往美国。机票已订好,一切手续均有效。如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均可满足……”
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官员指出:在预定的时间,苏联驻日使馆一等秘书来到了专门隔开的房间。3名保卫人员占据了“战斗部位”,眼睛直盯着他。之后,别连科在另3名安全人员的陪伴下也走进了房间。别连科盯着双脚,甚至连招呼都没同目已的同胞打。当别连科在15米长的桌子的另一端坐定后,苏联外交官抬起头来说:“我是苏联大使馆代表。您的同志请我们转达,在这对您来说不轻松的时刻他们同您在一起。苏联政府知道,您对发生的事件没有责任。我们清楚,您并非自愿在日本降落的。您偏离了航线,您是迫降的。我们知道,不顾您的抗议,您被投入了监狱,日本人对您施用了麻醉剂。不过,即使假定您犯有错误,我们坚信您也没犯我说的错误。即使犯了这种错误,在此情况下我可以以中央的名义向您保证,您将会受到宽恕。我来此是想帮助您回家的,回到亲爱的妻子、儿子和亲人身边……”
别连科没让他说完。他站起身来,像先前那样避开外交官的眼睛,嘟嚷道:“我是自愿飞到日本来的……我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不必劝说我……”
“叛徒!”外交官恶狠狠地大声对他说。“您知道叛徒的下场!我们迟早会把你抓回去的。不论你呆在何处,我们都会找到你!”
日本情报部门的主要官员显然对案件的这种转折感到满意,他关掉了录音机,微笑着对苏联外交官说:“您可以随意了,我们不再打搅您了。”
在后间,日本外务省代表对别连科说:“您表现得太好了。”他递给别连科一瓶俄国伏特加酒。别连科提议马上同“日本朋友”喝干它。
当天深夜,由加强民警勤务班保护的汽车把别连科送到了机场,那里停放着等待起飞的波音-747客机。
头等舱已为苏联飞行员随行组包下,别连科在日停留期间每天见面的美国人吉姆已等候在那里。飞机起飞后,吉姆拍了一下别连科的肩膀微笑着说:“我们飞走了!现在等待您的是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
机组人员给叛逃者送来了一瓶俄国伏特加酒,供其消磨时间。别连科有了醉意,话多起来,请示提出更多的问题。当大家都开始打盹后,他给自己斟了半杯酒。他也想睡会儿,却睡不着。后来在审问他时,他承认脑子里老排解不掉苏联大使馆代表“我们迟早会抓到你”这句话。
后来,在同“美国朋友”坦率交谈时,他这样描述自己横渡太平洋时的心态:“即使不对我起诉——这本身是难以置信的,我回去后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改变不了。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亲、母亲、姨妈会不会遭殃?未必。克格勒很容易弄清楚,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柳德米拉和儿子吉玛呢?也不会。她的双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那谁会遭殃?天晓得……” 别连科逃往日本那天,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在巴黎访问。记者们冲着他问:“美国将如何处置苏联叛逃者?”基辛格回答:“美国多半要向他提供政治避难。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认为我的意见一钱不值。”
第二天,1976年9月7日,福特总统得知了苏联飞行员的消息,接到了基辛格国务卿巴黎讲话的报告。他说:“应立即向苏联飞行员提供政治避难。”
这期间,苏联外交部向东京发出了照会,要求立即归还飞行员和战斗机。苏联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受命采取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接近飞机。就在别连科飞抵函馆的当天,机场办公室大楼就出现了苏联代表,他自称是“停靠在函馆港进行维修的苏联商船的船员”,请求允许同自己的同胞别连科交谈。
日本特别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他立即走开。但机场上很快又出现了3名苏联代表,其中一人自称是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另外两人是苏联民航公司代表。他们申明说,他们受托要把已损坏的飞机运送到苏联船只上。机场主任回答说:“很遗憾,飞机规处在警察的保护下,我无权满足你们的要求。”
苏联驻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向日本外务省长官宣读了一项声明,语气之严厉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声明断言,别连科是迫降的,指责日方是在“制造谎言”。莫斯科威胁说,如不交还飞行员和飞机,将导致“不良后果”。
如此强烈的外交压力,日本当局开始动摇了。日本外务省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出通报:东京开始“倾向于尽快归还苏联飞机,允许俄国人保留自己的面子”。这些话美国人连听都不愿意听,把飞机运往美国已列入五角大楼的计划。
美国前国防部长道纳尔特·鲁斯费尔德回忆说:“当时我们需要米格飞机,需要查明它是由何种金属材料制造出来的,试验它在不同状态下的飞行情况,还想将它拆散,然后再复原并飞向天空。”
华盛顿向日本提出了另一方案:让米格机在日本滞留一个月——这段时间对美国人仔细研究该战斗机已经足够了。日本人同意这一方案,条件是:美国人一定要着便装工作,日本专家参与观察。很快,莫斯科从其在美国和日本的谍报人员那里得到密报:一大批美国军事人员已到达函馆,以便拆卸“米格”飞机。苏联驻东京大使向总部报告说:制止对飞机研究的良机再也没有了……
然而莫斯科对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仍在继续。美国国会执行赫尔辛基协议专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收到了别连科妻子柳德米拉的一封信:她呼吁美国国会议员“重申自己忠于人权的原则”。苏联大使馆高级代表尤利·沃隆佐夫来到美国国务院,要求同别连科进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见”。
莫斯科的苏联外交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活动。下面是在这里举行的苏联和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摘录。
“我们的飞行员并非预先有意飞往日本……当不明身份的人试图接近飞机及为抗议对飞机拍照,他警告性地开了枪,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日本当局对飞行员施用了暴力。送往监狱时,他被戴上了手铐,脑袋上蒙上了某种袋子,然后被推入了汽车座……美日合伙劫持别连科——这是冷酷无情之人的随心所欲行为及对不久前福特总统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的粗暴践踏……”
但过了数日,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白宫同福特总统会见时,却以完全不同的语气谈起了别连科:
“我们坚持要求返还飞机,并非因为担心我们的军事秘密会落入他人之手,而是因为飞机被盗了。别连科是窃贼,是叛徒,是刑事罪犯。根据国际法准则,美国有责任将他交出。作为窃取了飞机的刑事犯,他不能要求政治避难。按国际惯例,别连科应被遣送回苏联,并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
福特皱着眉头听完了葛罗米柯的意见,然后以他不曾有过的生硬态度郑重地说:“别连科是难民,他有一切理由要求避难。美国乐意向他提供在这里生活的机会,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既然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归美国政府管辖,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勿须再讨论了。”
听完了这些话,葛罗米柯借口莫斯科有紧急事情要办而拒绝了建议中的午餐。
陪同别连科去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批官员乘坐的波音747客机,在洛杉矶机场降落了。负责保护别连科的吉姆,给了他一顶假发和一副墨镜,并解释说,这是为了不让当地人认出他。舷梯旁已有中情局的汽车在等候,别连科及其保缥乘坐该车向邻近的机场疾驶,那里有一架不大的客机在等候他们。
别连科有些激动不安,飞机刚一起飞,他就对同路人提出:准备回答任何问题!这一请求看来有点唐突。陪同组组长笑了一下说:“安静点,凡事各有其时嘛。”飞机降落在华盛顿达拉斯机场。一小时后,别连科被安排到了一幢秘密大楼,并送来了晚餐,晚餐后他很快睡着了。
早晨,黑人男仆叫醒广他。早饭后吉姆把他介绍给广一个叫“彼得”的神秘人物。之后又介绍给了“尼克”。别连科明白,“美国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开始同他工作了”。
谈话进行了许多小时,大家都累了。作为奖赏,彼得和尼克建议别连科游览一下城市,看看超市。这也是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应使苏联飞行员对美国的富有大吃一惊。他被从头到脚重新包装了一番。别连科欣喜若狂,不时地握着新朋友的手说:“谢谢你!……”
很快,别连科又被交给了一个叫安娜的女人,她是乘一辆红色轿车出现在别墅的。从所提问题看,她是持不同政见方面的专家,校正了叛逃者的某些反苏观点。安娜通过对苏联生活中阴暗面绘声绘色的描绘,为土头土脑的别连科彻底洗了脑。然后又以“前所未有的功勋”之类的恭维话为别连科大唱赞歌,使别连科深受鼓舞。他的话随之多了起来,同安娜闹扯了几乎一整天,而不是原先预定的4小时。
中情局的航空技术专家则想尽快提讯别连科。他们提出每天同他进行4小时时谈话,但却遭到了心理学家的反对:只有上午前两个小时对“招供”富有成效,否则飞行员疲惫的大脑可能会漏掉重要的细节。
第一次工作时,美国人问叛逃者承认,他们害怕拆卸“米格”飞机,并说明了原因......
在歼击机驾驶舱,他们看到了一个写有“危险”的红色按钮。美国人猜想,飞行员只有在被弹出舱前或在国外迫降时才能按它。中情局的专家估计,按钮将使爆炸设备启动,以便炸毁飞机上最保密的装置。美国人不排除,爆炸有可能在瞬间将飞行员和飞机一起毁掉……因此,为便于聆讯别连科,他们带来了已放大至真实尺寸巨清晰度极高的飞机机舱的巨幅照片。主持聆讯的是一位美国空军上校。照片被垂直放置在地面,别连科坐在他们之间的椅子上详细地回答着问题。问题很多。停顿只有一次——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某些写有“危险”的按钮下面的保护销被取下来了。这使美国电行专家高度警惕起来:他们对飞机可能爆炸的担心增加了。于是美国人制作了销子,补装了上去。
根据美国别连科案件主管翰·巴朗提供的证据,当天在苏联飞行员和美国上校之间还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
“请给我演示一下怎样启动发动机。“
“您为什么不想等飞机运来后再说?”
“担心我们没机会同您一起驾驶这架飞机了。”
“什么?您疯了?!”别连科变成了另一个人。“归还飞机?要是你们的F-14或F-15降落在了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把它归还给你们吗?!现在这是我们的飞机!我冒着生命危险把它给你们了!为把它转交给你们,我失去了一切!把我的飞机从日本人那押运来!如果你们要归还,苏联人会耻笑你们的。他们会把你们看作傻瓜!”
“安静点!”那位美国上校说。“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我不搞政治。我们指望在您的帮助下,即使不驾机飞行也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它。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工作......”
“我不回去......”
莫斯科并未失去把别连科遣送回同的希望。苏联大使馆参赞尤里·沃隆佐夫前来同他举行例行会见。谈后没有离开原地的提纲:外交官劝导飞行员说,他是后果严重的事态的牺牲者。“如果您返回祖国,您将会得到宽恕。”别连科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还在东京时就已死记硬背的那些话:“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向我提供什何麻醉剂,我自己决定要住在美国。我不回去......”
仍旧提出了迄今没有明确回答的那个问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别连科以警觉且略带愚蠢的眼神注视着沃隆佐夫,最后逼出了一句话:“您可以自己猜想是为什么......”
告别时沃隆佐夫告诉别连科:“我们相信您还会回来的。您会重新同我们在一起。这一天要来的!”
谈话后别连科走进了后面的房间,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在去别墅的路上,特工们将别连科带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并沿着狭窄的小径绕来绕去。别连科开始不安起来: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我们想看看是否有克格勃的密探盯我们的梢。”
“当然!这点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一危险您后半生都得记住……”
差不多有10年时间,米格-25成了美国情报机构挥之不去的头痛病。关于这一点有本书里说:“美国专家不明白,他们的苏联对手怎么在60年代就能制造出不仅飞行速度超过音速2倍,而且还能在27000米高空携带4枚威力强大的重型导弹这样的歼击机。美国在70年代制造的最新型的歼击机,都难以达到这一点......”
美国情报机构几乎用了10年时间企图打探神奇歼击机的秘密而毫无结果,别连科却给送去了中情局连做梦都没梦见的礼物。叛逃者驾驶的在函馆降落的飞机,是1976年2月出厂的——诞生总共才只有半年.
200多名美国飞机制造、武器装备、电子、冶金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专家把“飞机开了膛”,在拆卸分解过程中,拍摄了数千张照片,然后又把拆散的“米格”机装入巨型运输机,最短的航程运抵美国。
莫斯科知道了这一行动。苏联总参谋部有位高级参谋昏头昏脑地产生了制造运输机事故的念头,但这一想法立即遭到了否决——这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国际丑闻,日本人和美国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一个协同动作的“鬼怪”机群在尽可能远离日本领土的空域内为运输机护航,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空军机群在太平洋上空对“贵重货物”进行保护……
当“米格”飞机被横过来竖过去进行研究的时候,一位美国专家得出结论说:“是的,我们猜想这是一种极好的飞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它能比这一级别的飞机飞得更高、更快及携带更重的物体……”另一位专家的看法是:“美国应该邀请俄国的设计师,请他们教我们如何经济地设计和制造……”美国空军情报部主任吉姆将军含糊不清地承认:“这种飞机的制造过程,反映出俄罗斯人极善于用取之不尽的发明才智来弥补资源的局限。他们非常巧妙地把新老工艺结合起来,在较短时间内及花费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出了这种战术技术性能的飞机,西方要达到这样的性能则需要投入巨额经费。” 每天对别连科的聆讯差不多持续了半年时间。最后,当他身上一切可能的情报被“榨干”后,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置这个逃犯呢?中情局在征得国会和政府同意后,建立了专项基金,该项基金可保证叛徒“物质生活上的独立,直至生命的结束”。钱被存放在华盛顿一家银行的账号上。那些日子,中情局给叛逃者更改了姓名,发给了相应的文件。他曾冒充挪威人在一所大学读完了短期英语训练班,最后隐匿在了美国偏僻地区的一家农场。起初他在这家农场养猪喂牛,挖壕沟,建粮仓,修机器。
“农场主”有特别密码同中情局联络。用约定的电话呼叫密码后,别连科立即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农场主有一架私人飞机,从新颖性判断,是在他到来之前配置的。别连科驾驶它做了高级特技飞行,最后露了马脚。继续以农业工人的身份呆在农场变得危险了,特别情报处长要他住在“易于失踪”的大城市,认真在大学学习英语。
这时别连科购买了一辆高级轿车,花去了他不少钞票。归他支配的基金实际上相当有限。住豪华套间太不合算,他在工作住宅区重新租赁了便宜的套间。他又开始在大学学习。这时他曾短时间同西班牙女郎玛利娅热恋,但这位姑娘很快离开了美国。同姑娘分手对别连科的精神打击很大。他辍学了。
他感到孤独,越来越贪杯。一次他酒醉驾车,途中发生了车祸,为此曾受到中情局主子的严厉斥责。莫斯科很快知道了这一消息——更名改姓当然瞒不过专职情报人员。美国情报部门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对外散布消息说,别连科在车祸中丧生了。
一次,“丧生者”的神经系统驱使他驾车去了华盛顿。沿途,他曾因3次超速被警察罚款。他急欲想见中情局自己的上司彼得,彼得以对待失去理智者的眼神会见了别连科,因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允许他来此见面的。
别连科急不可耐地开始瞎扯起来:
“彼得,我有一个想法!您把我派到苏联去当间谍吧。把我投放到远东地区,我指给您看在什么地方。那里我熟悉,我会很容易完成任务的!你们美国人从来也不会明白,这个国家不论是谁和什么都可以收买。法官吗? 200卢布。企业经理500,军官50。不过,我们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不必购买。我能给你们搞到‘米格’或‘逆火’式轰炸机!我说运到哪里,我的朋友就可将它们运到哪里。派我去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听完别连科这段狂妄的大话,彼得恶狠狠地批他,极不满意他这种越轨的举动,劝他再去找找医生。医生给别连科开的处方是“积极休息”。于是他便驾车四处闲逛,以摆脱报应幽灵的纠缠。一次,他向他的美国保护人招认:一段时间里,下意识地渴望回国的念头紧紧地包围着他,使他不能自拔,甚至发展到几乎要将汽车开向苏联驻美使馆的大门……
他再次奔向彼得,早晨4时便把彼得叫醒。听完了受援人怀乡病的表露,彼得说:“免疫力会培养起来的……”
不久,别连科对自己的主子说,他希望驾驶商业飞机。经专业培训班培训后,美国人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时间最能冲淡记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想起别连科叛逃事件。
我们到美国寻找他的踪迹,当我们向当地的一个特别机构提出采访别连科的要求时。他们对我说:“啊,这是不可能的!您的老乡要求记者支付一大笔钱,有时还要女人......”
我只好请他们向别连科转达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日本的?”看了这个问题,一个美国特工微笑了:“我们迄今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我们20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转告了我的问题,别连科一直保持沉默。这时我熟识的一位掌握重要秘密的美国情报人员向我建议:“想见见您的同胞吗?请在机场等候,也许您有这个运气…”